今年是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李景均先生著作的英文版《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出版70周年。該書是中國現代史上迄今為止極少數在中國出版但在西方某個科技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專業書。絕大多數新中國成立后出生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李景均是誰。在美留學的大陸學生,除非所學專業和人類遺傳學有關,恐怕大多數也不知道李景均是誰。而在1950年的遺傳學界,恐怕大多數人都知道李景均。李景均先生的離國出走,在50年代初甚至還驚動了中央的最高層。
筆者和李景均先生(在美人們都親切地稱其為CC,以下簡稱為CC)的相識是在1997 年。針對《科學》雜志上一篇有關中國基因大戰的報道[1],筆者在97年9月起草了一封致《科學》編輯部的信,email給一位對遺傳流行病學頗有造詣的朋友鄭長江(CJ)博士。CJ當時正在匹茲堡作實習醫師。他是一位很仔細的學者,對信作了修改,并建議我們請CC一起署名。這就造就了筆者和CC的一段緣分。
97年的來信發表之后[2],由于西方遺傳學家就中國《母嬰保健法》的部分條款似有強制性的優生學之嫌而欲抵制在北京召開的第18屆全球遺傳學大會,筆者、CJ和CC就此在98年寫了另一篇評論[3]。之后,在98年在丹佛召開的美國人類遺傳學年會上,筆者和CC及其太太見了面。后來,老先生又給筆者寄來了刊登在《炎黃春秋》的關于他本人的一篇報道,以及他寫的一些教科書。我們還就其他一些事有過通信。
當然,筆者對CC的了解并非局限于這些溝通。作為科學家傳記及訃告的讀者,筆者以前也讀過斯皮思(E. B. Spiess)寫的關于CC的極富傳奇色彩的生平介紹[4]。在CC的處女作出版70周年之際,本文旨在回顧李先生那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生,緬懷李先生遺留給我們的豐富精神遺產,并對李先生離國出走的教訓及其現實意義作一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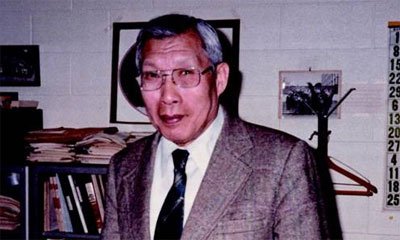
不能記住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
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
CC的人生可以說是極富傳奇色彩。CC于1912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大沽的一個做桐油生意的富商之家。其父曾在英國傳教士辦的學校念書,之后皈依基督教。他有四個兒子,CC是其第三個兒子。CC 13歲時,進了也是英國傳教士辦的天津英中學院(一所高中)。1932至1936年在美國傳教士辦的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念書,1937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學習植物育種及遺傳,1940年獲博士學位。留美期間,CC 閱讀了著名遺傳學家杜布詹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遺傳及物種起源》,由此接觸到了群體遺傳學以及賴特(S. Wright)的工作,并對此深感興趣,決定以此作為研究方向。拿到博士學位后,CC去賴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學上了一個夏季的數學和概率論課程,并在賴特的影響下去哥倫比亞大學及北卡羅來納大學進修數學和統計學。CC在芝加哥認識了后來成為其妻子的美籍華人克拉拉(Clara Lem)。1941年9月,CC與克拉拉完婚,并攜新婚妻子在圣地亞哥登上一艘準備開往上海的荷蘭郵輪,開始了蜜月之旅。
坎坷的回國之旅
1941年的中國,正在日寇的鐵蹄下遭受蹂躪,CC在美國對此無疑非常清楚。而攜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妻子回國,顯然是準備回國施展才華,報效國家的。這艘原本三周到達上海的郵輪,由于要避免遭受在太平洋水下游弋的日軍潛艇的攻擊而多次改變航向,輾轉在爪哇島補充給養之后又向上海開去。未到上海,就被轉到一艘英國船上。而這艘英國船在開往上海的途中聽說上海滿街都是日本軍人,擔心船只被日軍扣留,就轉而往香港開去,結果輾轉51天后在12月 6日抵達九龍。12月8日,CC 和妻子用完早餐后聽見了槍聲,并驚訝地發現所有的商店都關門大吉——原來當天日本偷襲了珍珠港(香港和夏威夷有一天的時差),并幾乎同時進攻香港。駐港英軍節節敗退。結果CC和克拉拉被困在香港近兩個月。由于他只帶了旅行支票而無人愿意兌現,他們兩人身無分文,十分窘迫,天天處于極度饑餓之中。57年后, CC回憶起當時的困境時說:“如果你處于極度饑餓時,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5]
就在這時,命運女神眷顧了CC。他遇見了在康奈爾念書時認識的朋友。朋友給了他500元港幣及一些大米。之后,CC又認識了一個香港地下組織的人,幫助CC夫婦徒步繞過日軍,跋山涉水,千辛萬苦到達廣東惠陽,再從惠陽再乘船坐車抵達CC一個哥哥所在的桂林。從九龍到桂林,花了整整38 天。
1942年6月,CC的第一個孩子Jeff出生了,但出生后沒幾個小時,克拉拉就抱著嬰兒為躲避日軍的空襲而躲進了山洞。當時CC的父親在重慶,由于戰時交通不便,CC就在廣西柳州郊外沙塘的廣西大學農學院任職。在這里,CC認識了兩位分別對中國及世界遺傳學都有影響的同道:劉祖洞和徐道覺。劉祖洞先生后來去美國密歇根大學學習動物學,1952年取得博士學位后翌年回國,在復旦任職,專長人類遺傳學和醫學遺傳學。劉祖洞教授編寫的《遺傳學》教材是國內遺傳學教材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教科書。劉先生在1956年青島會議上旗幟鮮明,思路清晰,言辭犀利,令人印象深刻。若不是歷場政治運動的耽誤,劉先生必有驕人的學術貢獻。劉祖洞先生于1998年辭世。
徐道覺先生那時與CC很熟。徐“好學不倦。他全身上下至少有8個口袋,上身有4個,褲子又有4個。每一個口袋都裝有昆蟲或其食物(在玻璃瓶子里)。”CC稱其為“會走路的實驗室”。CC當時斷言:徐將來必成大器。果然,徐在1951年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獲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中創造性地把組織培養技術和低滲處理用于研究染色體,為創建遺傳學的一門新分支——細胞遺傳學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令人扼腕的是,盡管當時人體細胞的染色體數目被錯誤地認為是48,且徐先生發現的技術為觀測人體細胞的染色體提供了有力手段,但他還是與改正人染色體數目的機會失之交臂。令人欣慰的是,他此后又作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工作。由于其杰出貢獻,他于1973年當選為美國細胞生物學會主席,2003年故世。
1943年夏,CC想去重慶看望其父,然后去成都赴遷至成都的母校南京金陵大學任教。但在去重慶的路上,CC的小孩患痢疾,結果CC一家趕緊坐火車回柳州看醫生。不幸的是,Jeff在火車上死在CC的懷抱中。Jeff不幸夭折,CC夫婦倆的悲痛可想而知。之后,CC在1948年及 1955年再版的《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的扉頁上都寫明,書是紀念Jeff的[6].
北平:短暫的蜜月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CC一家隨校舉家遷往南京。同年,其金陵大學的導師出任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他邀請CC出任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系主任兼農業試驗場場長,CC欣然前往。此時CC才34歲,為北京大學當時最年輕的一位系主任。
1948年,CC的英文版《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CC在 1946年至1948年撰寫的。該書的完成,用CC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半來自自己的腦子,一半基于在成都時抄寫的文章”。該書出版后的第二年,CC在美國的弟弟自費翻印了500本,在美國出版。
1949年9月,北大、清華、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并,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在校務委員會主任樂天宇(行校長職,兼黨總支書記)主持下,學校效法蘇聯李森科1948年“消滅”摩爾根學派的做法,停止CC主講的《遺傳學》、《田間設計》和《生物統計》三門課程,并將CC的《遺傳學》換成李森科學派的“新遺傳學”。樂天宇認為,這些課程是“資產階級的”、“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服務的”、“唯心的”、“反動的”、“偽科學”,“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 CC從此無課可上,被晾在了一邊。
盡管樂天宇僅僅是校務委員會主任而無任何行政頭銜,但憑借其老革命的資歷及執政黨的地位,樂天宇的話遠較當時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的話有分量。不久,CC間接地接到一個要他辭去系主任的消息,他第二天就辭去了系主任的職務。樂天宇及其隨從曾試圖在CC 手下招募一些能批判CC的人,但均未成功。
隨著對摩爾根學派的詆毀攻擊甚囂塵上,對個人的批判打擊也逐漸增多。令人噴飯的是,一個李森科的追隨者發現,除了摩爾根,還有一位叫 “Melanogaste博士”的“反動遺傳學家”!(作者注: Melanogaste為黑腹果蠅的學名).
當時對CC 的一個指責是,CC是在反動教育系統下培養出來的人,從未接觸過“進步”思想,所以不懂李森科學派的新概念。為了證明這個指責是毫無根據的,從1949年 7月開始,CC與陳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遺傳及其變異》,根據杜布詹斯基的英譯本翻成中文出版。與陳延熙副教授的合作,一方面是因為CC與陳交情較深,且陳的中文更為流暢,另一方面也因為陳與官方關系良好,翻譯完后出版的機會更大一些。事實上,樂氏在得知CC 在翻譯李森科的書時就極力阻擾,并散布謠言說,CC的譯本是根據另一個“反革命遺傳學家”(指杜布詹斯基)的英譯本翻譯的,只能歪曲李森科的學說。幸運的是,經胡喬木審閱后,這本譯著很快出版了,且出版后僅幾周就售出了幾千本之多。
CC為該譯著寫了一篇意味深長的《譯序》。他寫道:“農學博士、列寧全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院士的轟動世界的遺傳理論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書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在這本書里,誠如齊門乃夫所說,他闡發了米丘林遺傳學的理論基礎。”“這本書是一本理論著作,必得仔細研讀體會,才能了解其理論的真諦。”整個序言不失客觀尊重,亦無嬌枉做作粉飾獻媚之嫌。
這本出版于1950年1月的譯著和這篇《譯序》,充分表明CC對于米丘林學說及李森科學派并非他人所說的那樣是一竅不通。
隨著《遺傳及其變異》譯著的出版,CC對米丘林學說及李森科學派一竅不通的謊言不攻自破。樂天宇之流就又換了一種伎倆。他們又散布謠言說,CC 曾罵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在當時,官方的政策是向蘇聯“一邊倒”,任何批評蘇聯的言論都可視為間接批評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因此,這種對蘇聯的稱呼不啻為一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可置人于死地的言論,還有人說,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華人,好幾次去美國大使館(當時尚未撤走),“不知道他們搞什么鬼”。這些謠言和言論,無非是想把CC描繪成親美反蘇的“反動分子”。其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的伎倆,令人扼腕。
離國出走
新中國成立前夕,CC曾于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長葉劍英表達了要為新中國科教事業貢獻力量的熱忱心愿。然而,在樂氏等人日益變本加厲的迫害下,CC認為,“把一個純學術問題扣上政治帽子,變成人身攻擊,誣蔑為敵人,不能容忍”。所以,“即使有極大的耐心,我的同事們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國把遺傳學從滅亡中拯救出來。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聲明忠于李森科學說,否則只有離開。”他感覺自己“一腔熱情,報國無門”,“所學無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CC決定離國出走。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離國出走極有可能被認為是叛國,所以風險極大。1950年2月寒假,CC在上海的母親病重。CC認為時機已到,遂將幾個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計劃向克拉拉和盤托出。為減少風險,夫婦倆決定將出走之事做得隱蔽一些,甚至把家里的米缸加滿了米,使人看起來他們還準備回來。
1950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CC夫婦一直沒有入睡。午夜之后,CC悄悄敲響了鄰居林傳光教授的門。林教授開門一看,CC正神情沮喪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別,CC即將挈婦攜雛遠渡重洋。林教授一時目瞪口呆,竟不知說什么好。等到CC告辭回去了,林教授這才完全醒悟過來,趕忙穿好衣服,趕到CC家,勸告CC萬萬不可出此下策。否則萬一被捕,那時就后悔莫及了。但CC去意已決,不愿臣服于樂天宇而茍且偷生。不論林教授如何懇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CC一家由北京農業大學宿舍去前門火車站。臨走之前,CC特意給校委會主任樂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紱留下一封信,信中稱“身體欠佳,請假數月,請勿發薪”。到達火車站時,俞大紱率陳延熙、王煥如、陳道等副教授冒著春寒送行,“揮淚拜別”。盡管CC 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來,但大家心里都有些數,只是裝著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別,共事多年的好友從此永隔天涯。
在上海呆了兩天后,CC一家坐火車去廣州。1950年3月12日,CC 懷里抱著4歲的女兒和克拉拉走過了通往香港的羅湖橋。在橋的另一端,CC的二哥正等著他們。他將CC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龍的公寓里,CC在那里住了14 個月。
CC在當時為什么會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拋棄所有家產而離開中國呢?須知那是在1950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三反五反,反右遠遠還沒有開始。知識分子由于學術見解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國還是聞所未聞的事。除非萬不得已,一般人不會傾家蕩產離家出走。
所有關于CC的傳記/回憶錄對此大多語焉不詳,而CC本人在1998年匹茲堡大學校刊記者所作的一次談訪中也僅僅說:“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是似是而非模棱兩可(double-talk)。對張三,你說這,對李四,你說那。其次,你不要對任何人說再見”[5].
事實上,在當局得知CC離滬幾天之后,CC在北京的家里就來了幾位不速之客。他們將家里搜查了一遍,但也沒搜出任何可疑之處,結果就派人在CC家駐守了幾天。
傾家蕩產、毅然決然地離家出走已經是不可思議,CC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煙幕彈來麻痹迷惑一些人呢?或許CC認識到,如果樂天宇之流能用造謠誣蔑的卑鄙手段來迫害CC,那么出走可能給樂氏等人授以實據,他們可能會用更卑劣險惡的手段來加害于他。而在這方面,類似的事已經發生在瓦維諾夫(Nikolay Ivanovich Vavilov, 1887-1943)身上。基于CC對蘇聯的了解,他對瓦維諾夫的悲慘命運應當說是有所了解的。
瓦維諾夫
我們都將走向焚尸爐
都將焚燒
但我們絕不會
從我們的信念后退
——瓦維諾夫
瓦維諾夫生于1887年。1913至1914年師從于遺傳學創始人之一的英國生物學家貝特森(William Bateson)。從1924年直至1940年被捕入獄,瓦維諾夫一直擔任位于列寧格勒的全蘇維埃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他在創建其種植植物起源中心理論的過程中,在列寧格勒創建了全世界最大的植物種子庫。該種子庫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達28個月之久而饑蜉叢生時還被完整地保存著——他的一個助手是在收藏有大量可食植物種子的種子庫內餓死的。他曾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全蘇地理學會會長,1926年獲列寧獎金。由于反對李森科的非孟德爾遺傳學,他于1940年被捕入獄,之后被指控為英國間諜、右派陰謀、與白俄有染、破壞蘇聯農業等罪行判處死刑。但據傳,其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試圖越境——他是在烏克蘭的西部邊境地區被捕的。或許是由于其導師的求情,抑或是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的妻子(瓦氏的師妹)的幫助,之后被改判為10年有期徒刑。在獄中還作了一百多小時的科學演講。1943年,他因營養不良死于獄中。
與CC一樣,瓦維諾夫在西方接受過教育,然后回國工作。但即便居全蘇維埃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及列寧獎金獲得者之尊,他最終也難逃獄中餓鬼一劫。而他CC 作為區區系主任,如果被指控為叛國,其命運必然多舛。或許這也是CC出走之前施放煙幕彈的原因之一?
37年后,CC在瓦維諾夫誕辰100周年之際,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發表在《遺傳雜志》(The Journal of Heredity)上[7]. 在同期期刊里,CC還發表了一篇書評[8],評論了一本書名為“李森科主義在中國”但其實是1956年青島遺傳學會議紀要的英譯本及注釋的書。令人回味的是,這篇紀念瓦維諾夫的短文提到了有關瓦維諾夫被捕主要原因的傳言。文章雖短,但仍然感覺到CC對瓦維諾夫在事業巔峰之時鋃鐺入獄、最終成囚中餓鬼的悲慘命運的惋惜。
自古英雄惜英雄。在唏噓瓦維諾夫悲慘命運之余,對比瓦氏,CC有沒有一絲對自己逃過一大劫的慶幸?我們不得而知。
在香港的逗留
CC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的教授聘書,歡迎他去臺大任教。隨聘書還附有校長的信,言明CC到臺大后倘若覺得不合意,校方將隨時提供方便幫助他去美國。但CC婉言謝絕了臺大的邀請。
CC到香港后寫信給在美國的朋友,告知摩爾根遺傳學在中國大陸的困境,并求助謀職,“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我將樂于為其效勞”。這位朋友將信轉給了《遺傳雜志》(穆勒當時為該期刊的編委之一),該期刊在1950年 6月刊登了這封信(顯然是征得CC同意之后),并冠以“遺傳學在中國死亡”的標題。
CC的這封信引起了美國著名遺傳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穆勒(Hermann J. Muller, 1890-1967)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關系,安排克洛(James Crow)對CC的書(當時已由CC在美國的弟弟在美自費翻印出版)寫了一篇書評,在《美國人類遺傳學》雜志發表。恰巧這時美國前任衛生部長派倫(Thomas Parran)博士剛剛走馬上任匹茲堡大學新組建的公共衛生研究院,欲聘一位人類遺傳學家,遂寫信給穆勒,希望能介紹一個人。穆勒隨即推薦了CC,并解釋說CC現在香港,來匹茲堡大學可能需要一些時日。考慮到推薦人是位諾貝爾獎得主,派倫表示愿意等待。隨后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生物統計系的系主任寫信給CC,聘CC為生物統計初級研究員。
然而,此時在香港的CC既無任何護照,也無任何可證明其國籍的證件,所以不能得到美領館的簽證。作為美國遺傳學會援助海外遺傳學家委員會、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及國際援救委員會的一員,穆勒和美國其他一些遺傳學家和美國國務院及美國駐香港總領館的官員就CC的簽證進行了大量通信。穆勒意識到問題是在駐香港總領館,于是他給總領館官員寫了這樣的一封介紹信:
美國遺傳學家們普遍認為,李博士所著的《群體遺傳學》一書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該書非常有助于培養在這一重要而難懂的領域里工作的年青科學家。
李雖年輕,但我認為,他是中國遺傳學界的領軍人物,且能面對極為困難的環境,擁有在其所從事的遺傳學領域繼續教學著作的勇氣。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拒絕在壓力下放棄自己原則的中國遺傳學家。我們十分期望能援救他,以期彰顯我們西方科學家對堅持科學自由的原則及向極權政府挑戰的英勇行為的贊賞。
此外,穆勒還為CC一家遞交了經濟擔保書。
到最后,由于沒有“身份證明”,簽證還是不能發出。1951年3月,穆勒在印度開完一個會議準備回美國之前,決定在香港停一下,希望看一下CC是否還需要什么幫助。到達香港后,CC一家邀請穆勒及領館的一位官員共進晚餐。大半個下午及晚餐幾乎都圍繞著CC展開,但該官員最后提出,CC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此時,穆勒馬上說:“這就奇怪了。在這間房間里,每個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誰是李博士,他就在這里。你還要其他什么身份證明?”這位官員就對CC說:“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不久,簽證就出來了。1951年5月,CC一家離開香港到達美國。
不出20年,人類遺傳學領域就多了一顆曦曦閃耀的明星。誠如西人所說,余下的就是歷史(The rest is history)。
穆勒為什么會對CC如此熱忱地幫助?
CC滯留香港時,穆勒已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美國人類遺傳學會第一任主席。其名聲自當時如日中天。他與CC非親非故,但對CC的幫助之大是有目共睹的。CC的人格魅力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這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穆勒在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極富社會正義感。他是摩爾根的學生,他在 20年代通過研究發現,X-射線可導致果蠅的基因突變。這項研究使穆勒在1946年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1932年,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穆勒對資本主義的前景逐漸悲觀。9月,穆勒去柏林準備和一位俄國遺傳學家短期合作。此時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在調查穆勒早期參與的一些政治活動。穆勒就去了蘇聯,并在列寧格勒主持了一個遺傳實驗室,繼續從事輻射與遺傳的研究。到了1936年,由于蘇聯國內政治上的壓抑,李森科的逐漸猖獗,加上斯大林對穆勒所著的一本關于優生學的書感到不滿,穆勒被迫離開蘇聯,從此對蘇聯希望破滅。1940年回到美國。1946年獲諾貝爾獎后,人們對不久前美國在廣島及長崎投放原子彈后所造成的巨大傷害記憶猶新,且逐漸升溫的冷戰及核軍備競賽使人們對核污染心存恐懼,加之穆勒是一位杰出的演講者,這使得穆勒成為一個很有影響也頗有爭議的公眾人物。穆勒回美國后,許多人仍然認為他左傾。
對蘇聯的希望破滅,加上在蘇聯期間耳聞目睹意識形態對科學的粗暴干預,對科學家的迫害乃至人身傷害,使得穆勒成為美國遺傳學會援助外國遺傳學家委員會、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及國際救援委員會等組織的一名活躍成員。聽到CC的遭遇,聯系到自己在蘇聯的遭遇及對蘇聯的希望和幻想破滅,或許使穆勒感到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幫助CC。這一點他完美無私地做到了。
CC也銘記著穆勒對自己的熱情幫助。1951年9月,CC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CC夫婦倆給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以紀念穆勒。
二 CC的《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及其重要學術貢獻
CC一生中寫了10本書,其中包括2本譯著。但是,他在1948年撰寫的處女作《群體遺傳學導論》(英文版,由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卻是對其命運起決定作用的一本書。 這本書是CC在1946年底至1948年初,以其在廣西大學、金陵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講稿為基礎的,但事實上為此書的準備從1944年就開始了。由于當時不具備任何科研條件,不可能做科研,CC就在搬遷到成都的金陵大學圖書館內系統地閱讀館藏的群體遺傳學文獻,常常將文獻抄寫在紙上。所以在撰寫《群體遺傳學導論》時,其內容已經是“一半在腦子里,一半在成都時抄寫的文獻里”。
群體遺傳學家克洛在一篇書評里對此書褒獎有加,也指出了一些疵瑕。克洛評論說:“隨著動植物育種學生以及人類遺傳工作者對群體遺傳學的興趣逐漸增長,這方面的入門教程非常緊缺。李教授這本極好的書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同時由于內容足夠詳細,亦可作為一本參考資料。該書第一次以書的形式搜集了費希爾(R. A. Fisher)、霍爾丹(J. B. S. Haldane)、賴特(S.Wright)等學者多得令人驚訝的大量工作,且均以清晰簡單的方法來闡述。”[9].
誠如克洛指出的,該書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介紹了費希爾、霍爾丹和賴特的工作。克洛還說,這三位群體遺傳學巨匠通常多用高深的數學來表述他們的問題及結果,這對許許多多學生物、醫學、動植物育種出身的人來說很不容易理解,所以在若干年里,費希爾,霍爾丹和賴特三位巨匠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要歸功于其(CC)將他們的成果變得更好理解。”
這本書的取材編排也是獨具匠心。從歷史淵源來說,群體遺傳學和人類遺傳學的發展幾乎是相互平行的。而CC的這本書一開始就介紹了人類遺傳學中常常用到的分離分析方法,然后才闡述了群體遺傳的各個方面,其中穿插了人類遺傳學中的不少實際問題。此外,每一章節還附有練習題,對自我測驗和進一步的理解不無幫助。
從時間上來說,《群體遺傳學導論》出版的時機是極佳的。該書出版之時已有幾本群體遺傳學及數量遺傳學的書,但它們均未涉及人類遺傳學,所以該書可以說是填補了一個真空。而人類遺傳學在1948年正處于起飛的前夜。《美國人類遺傳學》期刊在 1949年9月創刊。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共同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徐道覺在1953年發現了低滲透的溶液。1956年人類染色體的正確數目由華人蔣有興(Joe Hin Tjio)和列萬(A. Levan)給出。全世界第一個人類遺傳學系是1956年由尼爾(James Neel)在密歇根大學創建的。1959年,勒約納(Jerome Lejeune)發現先天愚型唐氏綜合癥是由21三體造成的。由此,遺傳學的一個新分支——醫學細胞遺傳學誕生了。
1955年,CC對《群體遺傳學導論》進行了一些修改,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斯皮思評價說:“該書對這一領域發揮的決定性影響達 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遺傳學家都得益于該書。事實上,要不是因為這本書,由費希爾、霍爾丹和賴特等偉人創立的基本原理在1970年前還只能為極少數人所理解。”21年后的1976年,李景均又出版了《群體遺傳學基本教程》,一般認為這是北京版的增訂版。
70年代后,由于基因重組技術的發明,人類遺傳學研究更是突飛猛進。到了80年代后期, DNA多態性標記逐漸為基因定位等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分子遺傳學的飛速發展,也刺激了群體遺傳學的發展。在群體遺傳學領域,60年代末70年代初木村資生(Motoo Kimura)提出的中性分子進化論,70年代尤文斯(Warran Ewens)提出的抽樣理論,以及金曼(J. F. C. Kingman)的溯祖理論(coalescent theory)大多運用了高深的概率論和隨機過程方法,沒有經過嚴格的數理統計科班訓練的人都很難理解,遑論作研究了。
此外,計算機及個人計算機的出現和普及,也為快速計算提供了可能。簡單分離分析也隨之為復雜分離分析所取代。到了90年代,人類遺傳學研究又轉向了利用家族系譜來進行人類疾病的基因定位。
盡管《群體遺傳學導論》中介紹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原理至今仍然有用,但它的用處已經逐漸讓位于一些內容更為現代的專業書籍。和其他發展迅速的學科一樣,再好的書也只能是各領風騷幾年或十幾年。但不管怎樣,《群體遺傳學導論》是一部首次向中國學術界介紹群體遺傳學的論著,一經面世就被學術界公認為名著,它對人類群體遺傳學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 CC的其他學術貢獻
CC對科學的貢獻遠遠不止《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除了對群體遺傳學的貢獻,CC對遺傳流行病的早期發展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創造了一種稱為“不計獨子女方法”(method of discarding the singleton)或簡稱“單法”(the singles method)的分離分析方法,簡單而實用。在計算機普及之前,它是遺傳流行病學研究中對疾病遺傳傳播規律進行分析的非常有用的方法。< /div>
在統計學方面,他也做出了驕人的貢獻。1964年,他的《試驗統計學導論》一書出版。這本書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實驗的統計設計原理及其方法,受到讀者歡迎。1975年,他的《通徑分析入門》第一次系統論述了通徑分析的原理、方法和應用。此書在遺傳流行病學研究領域曾十分風行,只是隨著個人計算機及統計軟件的普及,通徑分析才逐步讓位于結構方程模型。1982年,CC又出版了《不平衡數據的分析》,推動了統計方法的發展。< /div>
或許CC迄今為止影響最長久的一份學術精神遺產是他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臨床試驗的隨機 /雙盲兩個原則(作者注: 在比較新藥B和舊藥A時,隨機指參加試驗的病人被分到A組(服用A 藥)或B組(服用B藥)的機會均等。雙盲指病人分組前后,病人及觀察病人的醫生均不知病人在哪組)。50年代中期,美國25家退伍軍人醫院組成了一個評價癌癥藥物療效團體,CC被任命為該團體的生物統計學家。那時大規模的臨床試驗很少,也常常沒有生物統計學家的幫助。當CC提出要隨機化分配病人,并遵循雙盲原則時,遭到一些醫生的強烈反對。CC堅持己見,毫不讓步。幸運的是,當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負責人在理解了這兩個原則的原理之后,支持了CC,并威脅說,如果不采用CC的方法,他們將不提供資助。現在,這兩個原則已被普遍接受。隨機雙盲,尤其是隨機,再加上對照,是當今臨床試驗的基本原則,對客觀評價治療結果提供了方法學上的保證。在西方國家,新藥的審批極其嚴格。制藥公司在申請新藥生產出售許可證時,必須向國家藥物管理機構證明其所開發的新藥(或新的治療方法)確實有效。而其有效性的證明,必須有可靠的臨床試驗數據。一個成功的臨床試驗必須遵循隨機、對照的原則,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保持雙盲。未能遵循這些原則的臨床試驗的可靠性就會大打折扣。
CC還有著令人驚嘆的遠見卓識和堅持真理的勇氣。由于他在人類群體遺傳學的學術成就, 1976年CC受聘于美國國會控制杭廷頓病專家委員會。杭廷頓病是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呈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發病較晚,幾乎所有病人均為雜合子。在70年代,由于尚未找到致病基因,等到出現癥狀并明確診斷后,絕大多數病人已有了孩子。這樣,又有一半的人可能將致病基因傳到了下一代。所以,如果有一個基因檢測方法能檢測出雜合子,對病人及其家屬以及社會都是一個福音。
1977年,作為委員會的一員,CC提出:目前最迫切且實用的需要就是研究開發出一種有效的基因檢測方法,檢測出雜合子。這個檢測方法,伴之以有效的遺傳咨詢,從理論上來說可以將該病在一代內消除,使得該病的發病率降低到與新的基因突變幾率相當的程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個建議也是完全正確和切實可行的。不幸的是,該委員會執行秘書的見解與此大相徑庭。專家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強調了臨床及社會學需要,諸如尋找治愈杭廷頓病的方法,以及對病人給與經濟上的支持以及對病人的服務。CC 認為這與其提議沒有任何沖突。而事實上,在當時尚未找到致病基因且對致病機理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提出要尋找治愈杭廷頓病的方法,完全是不切實際的、近乎天方夜譚式的幻想。而且,最終報告還不無嘲諷地說:“遺傳咨詢并非治療杭廷頓病的靈丹妙藥……即使是強有力的優生學咨詢也不能清除該病……新的基因突變產生新的病人。只有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諸如脅迫、強制普查、絕育等措施或許能夠保證降低該病發病率……而即使該病的發病率降低了,那些病人的病情也不會有絲毫減少。”
CC對此撰寫了少數觀點報告,抨擊說,“這是我整個職業生涯中所聽到的最為荒謬的論點”,其有關遺傳咨詢實踐的描述完全是虛構的。通過撰寫少數觀點報告,CC旗幟鮮明地捍衛了自己的觀點。
16年后,杭廷頓病的致病基因在1993年被成功克隆。研究表明,該基因位于第四號染色體短臂。當該基因中的核苷酸CAG三體的重復片斷超過一定長度之后,就會導致杭廷頓病。而CAG三體重復片斷的長度具有一定的遺傳性。這些發現使得杭廷頓病發病前的基因檢測成為可能。CC在1977年的建議應當說是極有遠見的。
由于CC對于人類遺傳學的貢獻,1998年CC榮獲美國人類遺傳學會頒發的杰出教育獎。
CC的其它一些書及其對遺傳學、生物統計學的貢獻,由于已有文章,本文不再一一贅述。
四 CC的精神遺產
CC本人從未在公開場合標榜過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但其行動卻明白無誤地表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CC博士畢業后,以其學識和專業在美國找到一個教職并非難事。然而,CC放棄在美國舒適的生活工作條件,選擇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攜新婚妻子冒著生命危險回到祖國。如果沒有一顆報效祖國的雄心,恐怕不會做出此舉。CC在1949年向北京市首任市長葉劍英表示要為新中國科教事業貢獻力量,以其剛正不阿的性格,決非心血來潮或應景之舉。如葉篤莊先生一文所說,CC所教的北大農學院農學系1948年畢業16人,后來多已成為農業科研教學的骨干。他們對中國農業生產所做的貢獻,和CC的嘔心瀝血不無關系。2001年初,CC還將其所著《人口遺傳學初級教程》(First Course in Population Genetics)一書及其俄譯本寄贈給了中國農業大學。
1998年,在獲悉CC榮獲美國人類遺傳學會的杰出教育獎之后,匹茲堡大學的校刊《大學時報》采訪了CC [5]. CC講述了自己出生在大沽,那是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國登陸的地方。登陸后八國聯軍士兵在該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奸淫。登陸的次年,幾乎每家都有一個外國兵的小孩出生。村莊的年長者們作了一個決定:什么也不說,啥事都沒發生。幾千個嬰兒出生后還沒來得及哭叫就被掐死了。通過重新掀開歷史上這一鮮為人知、充滿屈辱的章節,CC很自然地表示出對大沽人民所受苦難的深切同情及對八國聯軍殘暴獸行無聲的控訴。
CC為真理絕不屈服的勇氣也是令人尊敬的。在淫威之下,許多人噤若寒蟬,惟命是從,更有少數人卑躬屈膝,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尊嚴。而一個人的屈從,又將進一步助長淫威,使更多的人俯首稱臣,賣身求榮。CC在樂天宇之流的淫威下,錚錚鐵骨,威武不屈,充分展現了人的尊嚴。這一點在中國恐怕很少人能做得到,也應該是我們永遠學習的。
五運氣和個人魅力
毫無疑問,CC的生平充滿了不少運氣和機遇。如果CC決定晚出走三四個月(屆時由于朝鮮戰爭爆發,出境要困難得多),如果當年CC的弟弟無力為他自費出版《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如果他在1950年時還心存幻想,留在國內,如果沒有穆勒不遺余力地為他的教職奔走,如果……他的命運恐怕會大不一樣。顯然,運氣在CC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就像巴斯德所說,機遇只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如果CC沒有過人的聰明和勤奮,再好的運氣恐怕也只能幫CC一時。
事實上,除了聰明和勤奮,CC還具有許多優良的品德及個性。CC具有將復雜的事講解得簡單易懂的不可思議的能力。他非常謙遜,從不居功自傲盛氣凌人。在和筆者的幾次通信中,他都尊稱筆者為“孫偉學兄”——而筆者那時還只是一所州立大學尚未拿到終身教職的副教授而已。CC非常慷慨,樂于助人,這在幾篇紀念CC的文章中都可看到[10-13]一旦別人有求,即使是難于啟齒的私事,CC都會放下手里的工作悉心傾聽,并提供自己的看法。CC還非常幽默開朗,這就很容易使人不知不覺地解除戒備而喜歡他。CC的英文有些口音。一次在大會發言時,他自我調侃說:“這個麥克風有中國口音,”引得全場哄堂大笑,氣氛頓時活躍起來。無怪乎CC在世時及去世后,有5篇講述其生平或紀念CC的文章發表,足見其口碑之佳[4, 10-14]。
CC當然也有他不走運的時候。由于一個美國科學院院士的阻撓(曾由于學術見解相異), CC雖獲院士提名但最終未能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對此他說,“當我50歲時,我覺得很重要很光榮,現在90歲了,日益淡泊,無所謂了”(2000年12月 22日給筆者來信),并不對此耿耿于懷。他還說,“我也有幸運的時候。1998年,我獲得ASHG的教育優異[秀]獎。我到達丹佛時,那個委員會的主席低聲告訴我:在評議時,是一致同意!”(2000年12月22日給筆者來信)
六哀莫大于心死
在1998年遇見CC時,筆者曾問他什么時候回國看看。他堅定地回答說,這輩子是不準備回國了。我也沒有再接著問原因。雖然CC從小接受的是教會學校的教育,也是在美國拿的博士,但他畢竟在中國度過了人生最初的25年。即使CC沒有“葉落歸根”的打算,但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對于自己在抗戰時親眼所見的百姓由于戰亂流離失所、妻離子散、餓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