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年里,癌癥免疫療法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誕生給腫瘤學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雖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卓越療效展示了人體免疫系統在對抗癌癥方面的巨大潛力,但是很多癌癥患者對這一創新療法并沒有響應。近些年來,人們經常會聽到腫瘤可以分為“熱”腫瘤和“冷”腫瘤兩大類型,這兩種類型的腫瘤有什么區別?對它們的治療方法有什么不同?有哪些手段可以提高癌癥免疫療法對“冷”腫瘤的療效?近日《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發表的一篇綜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答。今天我們將和讀者分享這一綜述中的重要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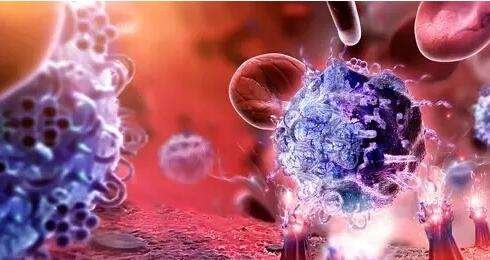
什么是“熱”和“冷”腫瘤?
目前對腫瘤和免疫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理解為將腫瘤根據其免疫特性進行分類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已有重要研究表明,在結直腸癌患者中,在腫瘤病灶處的免疫細胞的類型、密度和所處位置可以準確地預測患者的生存。這一研究導致了腫瘤免疫評分(Immunoscore)的產生。這一基于共識的標準化評分系統通過對腫瘤中心和腫瘤邊界(又稱為浸潤切緣,invasive margin)區域中的CD3+,和CD8+兩種淋巴細胞的量化統計,可分為4級。免疫評分為0的腫瘤在腫瘤中心和邊界區域都沒有CD3+和CD8+淋巴細胞,而免疫評分為4的腫瘤在腫瘤中心和邊界區域都存在高密度的CD3+和CD8+淋巴細胞。
目前人們經常提高的“熱”腫瘤和“冷”腫瘤指的是出現淋巴細胞浸潤和炎癥的腫瘤和沒有淋巴細胞浸潤和炎癥的腫瘤。這兩個概念與分數為4和分數為0的腫瘤有較好的對應關系。然而,除了“熱”和“冷”腫瘤以外,根據腫瘤的免疫特征,它們還有其它兩種類型:一種稱為“排除型”(excluded),這種類型的腫瘤邊緣存在大量CD3+和CD8+淋巴細胞,但是這些細胞無法浸潤到腫瘤中心。另一種稱為“免疫抑制型”(immunosuppressed),這種類型的腫瘤的中心和邊緣區域雖然都有淋巴細胞,但是細胞的密度不高。
癌癥免疫療法與已存在的免疫反應之間的關系
免疫調節策略的有效性與已存在的基線抗腫瘤免疫反應水平息息相關。對目前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的一個常見的比喻是它們去掉了免疫反應的“剎車”,但是這個比喻意味著原先“車子”是能往前跑的,如果原先“車子”沒有油了,根本就不會動,去掉“剎車”還是不會讓它跑起來。
已有的臨床研究表明,接受治療之前,在腫瘤局部或者在血液循環中已經存在的抗腫瘤免疫活性水平,對隨后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的療效起到重要作用。而效應T細胞的活性是抗癌反應的核心。CD8+ T細胞當識別腫瘤抗原后,能夠通過釋放大量細胞毒性因子來殺傷腫瘤細胞。在轉移性黑色素瘤患者中,在腫瘤邊緣出現CD8+ T細胞是PD-1阻斷能夠產生療效的先覺條件。而且,在產生響應的患者中,這一CD8+ T細胞群體的增殖與腫瘤的縮小有直接相關關系。通過打破免疫耐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能夠釋放已經存在的免疫反應來殺傷腫瘤,但是如果沒有已經存在的免疫反應,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則沒有效果(比如“冷“腫瘤和“排除型”腫瘤)。
作為單藥療法,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響應率在10-35%之間。大多數四期實體瘤在被確診時,原發瘤中沒有或只有很少浸潤的T淋巴細胞,這可能為患者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響應率提供了部分的解釋。為了提高這類療法的臨床效益,醫藥界展開了非常多的研究和臨床試驗來檢驗將不同免疫療法進行組合的療效,組合療法還包括將免疫療法與標準療法聯用。根據腫瘤是“熱”還是“冷”腫瘤,這些組合療法的療效也會有所不同。
“熱”腫瘤的治療方法
靶向T細胞的免疫療法
“熱”腫瘤因為已經包含大量的浸潤T細胞,它們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和組合療法嘗試的熱點。耗盡或功能失常的腫瘤浸潤淋巴細胞通常表達一系列免疫抑制受體,包括CTLA4和PD-1。靶向PD-1和CTLA4的療法已經獲得FDA批準,而且由于CTLA4和PD-1作用方式不重疊,它們是使用雙重免疫檢查點阻斷的好靶標。確實,抗CTLA4和PD-1的雙重阻斷療法已經在治療晚期黑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和腎細胞癌方面已經取得了成功,并且獲得了FDA批準。不過這些組合療法可能只會在“熱”和“免疫抑制型”腫瘤中產生效果,因為它們依賴于一定水平的浸潤T細胞的存在。
其它可以與PD-1藥物構成組合的療法包括靶向LAG3,TIM3, TIGIT的療法。這些靶點都屬于T淋巴細胞的共抑制受體。
另一種組合方法是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靶向共刺激受體的藥物聯用,這些共刺激受體包括OX40抗原(又名TNFRSF4或CD134), TNFRSF7(又稱為CD27),CD28, TNSFRSF9(又稱為4-1BB配體受體或CD137),以及GITR。這些受體的作用都是增強T細胞擴增和效應子功能,同時控制調節性T細胞的免疫抑制功能。
調控微生物組
抗生素在晚期癌癥患者中可能抑制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有試驗表明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反應和革蘭氏陰性共生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水平相關。因此,有選擇性地對腸道微生物種群成分的調節可能幫助克服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抗性。“好”細菌的數量增多與在血液循環中CD4+和CD8+ T細胞的數量增多相關,在黑色素瘤患者中,它們與對抗PD-1療法的響應也相關。
單靠調節微生物組可能對非“熱”腫瘤產生療效,但是現有證據表明,通過相對簡單的生活習慣改變或服用“好”細菌可能幫助提高隨后的免疫療法的效率,特別是對“熱”腫瘤患者來說。
治療“排除型”和“免疫抑制型”腫瘤的療法
T細胞運送調控劑
在“排除型”腫瘤中,CD8+ T細胞會在腫瘤邊界聚集。這意味著宿主能夠產生T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但是T細胞無法侵入到腫瘤內部。這一現象可能有很多解釋。一個原因T細胞被排除在外可能是由于缺少募集T細胞的信號,包括知道T細胞運送的趨化因子。它們包括CXCL9, CXCL10, CXCL11, CCL2和CCL5等等。腫瘤中出現的基因和表觀遺傳變異可能抑制了它們的表達。可以想見,促進T細胞募集的治療策略可能在“排除型”腫瘤中克服對免疫檢查點阻斷的抗性。
目前的研究表明,使用表觀遺傳學調控劑提高腫瘤表達的趨化因子,和阻斷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都能夠募集更多T細胞,將“排除型”腫瘤變為“熱”腫瘤,從而提高共同進行的免疫療法的成功率。
破除物理和生化屏障
T細胞不能進入腫瘤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物理和生化障礙。腫瘤的另一個標志性特征是產生異常組織結構。腫瘤的血管網絡和很多細胞外基質蛋白的表達都發生了顯著變化。腫瘤的血管網絡通過導致黏附分子的調控失常防止T細胞的遷移,這是T細胞浸潤的一大障礙。腫瘤增生造成的缺氧環境也有利于產生免疫抑制的腫瘤微環境,缺氧的作用主要依靠HIF轉錄因子家族的作用。另一提高腫瘤微環境免疫抑制特性的信號通路ATP-腺苷信號通路。腫瘤中存在的CD39和CD73酶能夠將ATP轉化為腺苷,細胞外腺苷水平的升高可以產生一系列免疫抑制作用。
針對這些因素,靶向HIF,CD73, CD39和腺苷受體的抑制劑或者單克隆抗體已經被開發出來,它們正在不同臨床階段接受檢驗。
另一種改變腫瘤微環境的方法是將腫瘤周圍的血管網絡正常化。血管網絡正常化可以減少缺氧環境,提高1型輔助T淋巴細胞的浸潤和活性。因此抗血管增生療法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的聯用可能產生協同效應。
克服可溶性免疫抑制因子
在“免疫抑制型”腫瘤中,腫瘤病灶處出現免疫浸潤,但是免疫浸潤的程度不高,這意味著可能有廣泛的免疫抑制環境,而不是物理屏障在阻礙T細胞的募集。IL-10和TGFβ是目前研究最為廣泛的兩種阻礙抗癌免疫反應的可溶性因子。IL-10和TGFβ的功能之一是阻礙樹突狀細胞的分化、遷移和抗原呈現。這些功能對產生有效的抗腫瘤T細胞免疫反應至關重要。最近TGFβ抑制劑與抗PD-L1療法構成的組合療法在臨床試驗中表現處了一定療效。
調控局部適應性免疫反應的調控細胞
在腫瘤微環境中抑制局部適應性免疫反應的兩類重要細胞是調節性T細胞(Treg)和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因此,藥物研發人員正在探索靶向這兩類細胞的策略。特異性靶向在髓細胞中高度表達的PI3Kγ能夠重塑腫瘤微環境,并且在小鼠癌癥模型中提高細胞毒性T細胞介導的腫瘤縮小。這類藥物與PD-1阻斷療法構成的組合療法目前正在臨床試驗中接受檢驗。其它消除髓源性抑制細胞的策略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治療“冷”腫瘤的方法
腫瘤免疫評分為0的“冷”腫瘤,是最難于清除的腫瘤類型,它們通常與預后不良相關。克服缺乏已存在的免疫反應,將“冷”腫瘤變為“熱”腫瘤的策略,是將提高T細胞反應的觸發療法(例如腫瘤疫苗),與消除共抑制信號的療法(例如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或髓源性抑制細胞清除)和提高共刺激信號的療法相結合。這種多重療法組合策略的風險是組合療法的毒副作用也會同時增加,因此,對這些組合療法需要進行非常嚴格的評估。
放療
一種有望與免疫療法聯用的觸發療法為電離放療。目前放療遞送的精準度和導致的對免疫原性細胞希望信號通路的激活可能將腫瘤變為原位疫苗,從而不但能夠起到局部消滅腫瘤的效果,還能通過提高免疫反應對遠端腫瘤產生影響。放療介導的細胞損傷釋放的DNA可以導致STING介導的1型干擾素的生成,而這會提高T細胞介導的抗腫瘤免疫反應。這一過程需要CD103+樹突狀細胞對腫瘤的浸潤,因此對“冷”腫瘤的效果有限,但是對“排除型”腫瘤應該有效。放療與抗CTLA4抗體構成的組合療法已經在治療黑色素瘤和NSCLC方面顯著改善了治療效果。
化療
基因毒性化學療法可以導致腫瘤細胞出現更多基因突變,從而產生新表位,這會增強腫瘤細胞的免疫原性。然而,這些新抗原可能在腫瘤細胞中表達的水平很低,從而對免疫反應的影響不一定恨到。即便如此,能夠導致免疫原性細胞死亡的化療藥物(包括蒽環類藥物,環磷酰胺,紫杉醇等)能夠通過釋放損傷相關的分子模式(DAMPs)和激發凋亡信號通路等方式提高佐劑效應(adjuvanticity)。已有研究表明,在乳腺癌患者中進行的新輔助化療(NAC)可以提高腫瘤內CD8+ T細胞與FOXP3+ 細胞的比例,而且抗癌T細胞的擴征與對NAC的反應相關。
化療還可能通過脫靶效應激活免疫效應子,從而導致廣泛的免疫激活。目前積累的證據表明,化療不但能夠抑制腫瘤生長,還能夠在正向調節免疫系統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靶向療法
腫瘤相關抗原(TAA)負荷不足理論上會妨礙有效T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的產生。因此,提高腫瘤免疫原性的療法可能會對T細胞募集有益,從而提高腫瘤殺傷效果。促使腫瘤細胞表達TAA的療法可以提高腫瘤免疫原性。這些療法包括DNA去甲基化藥物,或者EGFR和MEK抑制劑。這些藥物的一個共同功能是能夠提高呈現抗原的MHC I復合體的表達,從而提高癌癥抗原的呈現。
基于DNA修復的療法
高突變負荷和預期的高新抗原負荷在肺癌和黑色素瘤患者中與免疫檢查點阻斷療法的臨床效益相關。因此,提高腫瘤細胞中新抗原負荷的療法理論上可以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用。在小鼠研究中,在結直腸癌、乳腺癌和胰腺癌細胞中導致DNA錯配修復(MMR)機制的失活可以引發基因組不穩定性,并且觸發免疫監察的發生。這項研究不但表明了新抗原負荷的重要性,而且指出抑制DNA損傷反應(DRR)對免疫療法的潛在影響。目前有多項阻斷DDR系統的藥物在臨床前和臨床期接受檢驗。
CAR-T療法
CAR-T療法是目前癌癥免疫療法的另一大新興領域。在治療血癌方面CAR-T療法已經獲得出色的療效。對于“冷”腫瘤來說,關鍵問題是CAR-T療法能否將“冷”腫瘤變為“熱”腫瘤。從目前的試驗結果來看,單靠CAR-T細胞可能無法完成這項任務。在不存在炎癥性T細胞的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注入的CAR-T療法無法運送到腫瘤部位,由于腫瘤部位缺乏募集T細胞的CXCL9和CXCL10趨向因子。
溶瘤療法
溶瘤病毒是天然或者基因工程改造的病毒,它們能夠有選擇性地感染并且在腫瘤細胞中復制,最終導致腫瘤細胞裂解。除了直接和局部的抗腫瘤活性以外,溶瘤病毒還可以激發強力,全身性,并且可能持久的抗腫瘤免疫反應。瀕死的腫瘤細胞會釋放TAAs和DAMPs,從而激發有效地抗腫瘤免疫反應。
溶瘤病毒需要在保留刺激免疫系統能力的同時,消除毒力因子,才能作為療法使用。很多在研病毒在臨床試驗中接受檢驗,其中包括腺病毒、HSV-1、脊髓灰質炎病毒、麻疹病毒等等。很多在研溶瘤病毒對在腫瘤細胞表面光過度表達的細胞表面蛋白具有天然的趨向性。例如,CD46和HVEM分別是麻疹病毒和HSV-1病毒進入細胞的受體。
T-VEC病毒是第一款FDA批準的治療無法切除黑色素瘤的溶瘤療法。一個將“冷”腫瘤“加熱”的治療策略是用溶瘤病毒作為觸發療法,將它與消除共抑制信號的療法相結合。在臨床試驗中,T-VEC與ipilimumab在無法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中聯用的抗癌活性強于ipilimumab單藥療法。在另一項1b期臨床試驗中,先使用T-VEC,然后使用抗PD-1抗體pembrolizumab在晚期黑色素瘤患者中達到高達62%的響應率。
基于腫瘤疫苗的療法
在發現腫瘤細胞中的新抗原之后,這些新抗原或者新抗原表位可以通過不同的平臺被呈現出來,包括使用腫瘤細胞提取物,RNA或DNA編碼的部分或全部蛋白,或者在樹突狀細胞中表達的重組病毒或細菌載體。額外添加疫苗佐劑可以進一步增強對TAA的免疫反應。雖然理論上腫瘤疫苗似乎非常有價值,但是在多項臨床試驗中它們的表現缺差強人意。這讓科學家們致力于揭示腫瘤疫苗效力不強的原因。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是抗腫瘤疫苗在已經被確診攜帶腫瘤的患者中接受檢驗,而這時候腫瘤的免疫抑制機制已經在發揮作用。
因此,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成功給腫瘤疫苗療法帶來了新的希望。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臨床研究表明體細胞突變負荷和隨后具有臨床益處的新抗原的出現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為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激發T細胞的抗癌癥疫苗聯用提供了理論基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以提供類似于疫苗佐劑的作用。這種組合有可能為攜帶“冷”腫瘤的患者提供益處。
開發抗癌癥疫苗的挑戰是找到作為疫苗的最佳抗原。可供選擇的抗原包括過度表達的自身蛋白(例如前列腺特異性抗原),在腫瘤和健康組織中表達量不同的蛋白,和新抗原。新抗原可能是開發抗腫瘤疫苗的理想抗原,因為它們只在腫瘤中存在,而且隨著腫瘤的進展不斷產生。而它的缺陷在于每個患者的新抗原都不相同,這意味著疫苗也需要個體化定制,延長了疫苗到達患者手中的時間。
在最近的一項臨床試驗中檢驗了一種同時靶向20個預測的個體化腫瘤新抗原的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在6名接種疫苗的患者中,4名在接種疫苗25個月之后沒有出現癌癥復發。而兩名出現復發的患者隨后接受了抗PD-1療法,并且獲得完全緩解,而且這些患者中新抗原特異性T細胞群增加。這一試驗不但為個體化基于疫苗的免疫療法鋪平了道路,還為驗證腫瘤疫苗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聯用的潛在療效提供了證據。
T細胞免疫調節因子
有多種細胞因子(包括IL-2, IL-7, IL-15, IL=21, IL-12, GM-CSF和IFNα)可以調節T細胞的增殖、生存以及功能。它們正在臨床試驗中接受檢驗,作為單藥療法或者組合療法的一員治療癌癥。IL-2是最早被用于作為癌癥免疫療法的細胞因子,它在治療腎細胞癌和黑色素瘤的試驗中取得過積極結果。但是IL-2對免疫系統的多重作用和嚴重副作用限制了它的應用可能。目前對IL-2的新一輪研究力圖發現能夠有傾向性地與表達在T細胞上的IL-2受體相結合的配體,比如Nektar公司的NKTR-214。這一在研療法已經在臨床試驗中被檢驗與抗PD-1抗體nivolumab構成組合療法治療多種癌癥。
與IL-2相關的細胞因子IL-15最近吸引了癌癥免疫療法學界的關注,因為它不具有IL-2的嚴重副作用,而且只會影響天然殺傷細胞,而不會影響調節性T細胞的擴增。目前對它的研究力求增加它的生物可利用性,因為它們會被腎臟迅速清除。
結語
近年來,個體化癌癥免疫療法的概念越來越得到重視。而個體化的癌癥免疫療法的前提是需要在患者確診時,對于患者的腫瘤和免疫反應相關的關鍵性參數進行精確的測量。這樣才能對患者進行嚴格分類并且用于指導下一步的療法選擇。根據腫瘤是“冷”、“熱”、“排除型”還是“免疫抑制型”,一系列不同的免疫治療策略被采用。腫瘤越“冷”,越需要結合多種療法才能取得顯著療效。不管使用哪種免疫治療策略,最終,將療效最大化都需要將不同免疫療法進行組合。
1月11日,由上海市抗癌協會主辦,上海市醫學會、健恒醫療協辦的“上海市抗癌協會第三期青年腫瘤臨床科學家沙龍”在上海市科學會堂舉行。圖片由主辦方提供上海市科協黨組成員、副主席陳馨在致辭中回顧了科學會堂的......
2024年12月29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慢阻肺早期疾病演進相關機制和靶標發現”2024年度進展交流會在杭州召開。會議由自然科學基金委醫學科學部主辦,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浙江大學醫學......
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維韋克·穆爾蒂3日警告說,飲酒與癌癥之間有直接關聯,會增加至少7種癌癥發生風險,應提高人們對飲酒危害的認識。穆爾蒂當天發布關于酒精與患癌風險的建議,包括在含酒精飲品的標簽上標注致癌風......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李亞平和尹琦團隊構建了基于腫瘤細胞膜囊泡的個性化納米疫苗。該疫苗通過向B細胞提供多重活化信號,觸發了抗腫瘤固有細胞和體液免疫應答,實現了高效抗腫瘤的作用。近日,相關研究成......
一、出臺背景近年來,全球和我國百日咳疫情回升,我國小月齡嬰兒和學齡兒童發病風險有所升高。根據我國百日咳等傳染病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為進一步加強對小月齡嬰兒和學齡兒童的免疫保護,國家疾控局、教育部、工業和......
水稻是重要的主食來源。真菌Magnaportheoryzae引起的稻瘟病是水稻的嚴重病害。有研究發現,抗病受體NLR類蛋白在植物免疫調控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在分子抗病育種中得到廣泛使用。而NLRs介導的......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科學家開發了一種創新的“分子GPS”技術,能夠引導免疫細胞特異性地定位到大腦,并在不損傷周圍健康組織的情況下有效殺死腫瘤。這項突破性研究發表在最近的《科學》雜志上。這項基于活細胞......
癌癥作為致死率較高的疾病之一,一直是人類亟待攻克的難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杜鵬教授和團隊,提出利用植物中的一種蛋白,抑制癌細胞的增殖,從而實現對惡性腫瘤的廣譜抗性。這種跨物種基因工程技術,為人類治療......
代謝重編程作為癌癥的一個顯著特征,體現在腫瘤對營養物質利用方式的改變上,這種變化有助于其無節制地生長和存活。過去幾十年,癌癥代謝研究主要聚焦于葡萄糖,特別是著名的Warburg效應,即癌細胞即便在有氧......
無論是人類還是細菌,生命過程中都會面臨病毒的威脅。你知道嗎?細菌雖然比人類簡單,卻也有自己的“免疫系統”用來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北京時間12月13日,中國藥科大學藥學院藥理系、重慶中國藥科大學創新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