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科大研究生導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研究員徐星院士與研究員張馳的指導下,他將建模、統計等定量分析的“新手段”帶到古生物學這一“古老”的學科。博士期間,他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成果,在Nature、PNAS、The Innovation等期刊上發表多篇優秀論文;他多次榮獲中國科學院院長獎與博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獲北京市優秀畢業生等多項榮譽。 與恐龍結緣 四五歲的小孩似乎都有一種天性,對神秘強大的事物充滿幻想、心馳神往。和很多小男孩一樣,我在那個時期也沉迷于科幻電影中的怪獸,喜歡看奧特曼、哥斯拉。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了《侏羅紀公園》以后,我開始了解到“恐龍”這個概念。恐龍作為一類體型巨大的已滅絕生物,能夠滿足小朋友漫無邊際的幻想,但是它們又真實存在過,使得它們相比于其它影視作品中的怪獸又多了幾分真實,這可能是恐龍最初吸引我的原因。 那個時候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自己畫恐龍,或者吵著家長帶我去有化石的博物館看恐龍。初二的時候,我在學校舊書市場上買了一本《中國國家地理:恐龍特輯》,并在書中認識了我現在的導師——古脊椎所的徐星院士。 進入高中以后,我開始嘗試一些科普創作和簡單的科研探索。慢慢地,我對古生物學的研究性質也有了一些認識,我認為古生物學基本是一門依賴新化石發現的描述性科學,至多就是增加一點簡單的定量分析,對滅絕物種的生態習性進行推測,但是并不涉及過多的數理統計和分子生物學的知識。 不過,徐老師在2014年發表的關于鳥類起源的綜述文章改變了我的認識。簡而言之,文中除了列出古生物學對鳥類恐龍起源學說提供的證據以外,還從發育生物學和基因組學的角度對一些形態演化的機制進行了解釋。我當時知識水平有限,無法完全理解文中的討論,然而卻朦朧地覺得自己雖然面對的是化石,但是解決生物演化這樣大的科學問題需要更多的知識儲備。 漸入佳境 高考結束后,我根據興趣選擇了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的古生物學專業。那年暑假,徐老師遞給我兩本書,一本是哈佛大學出版的《脊椎動物功能解剖學》,另一本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系統發育分析課程講義,并叮囑我本科期間如果學有余力就把這兩本書讀好,同時也告訴我古脊椎動物學雖然源于地質學,但是很多新的研究方向需要更多的生物學知識儲備。 我當時覺得非常難以置信,因為自己從未讀過700多頁的英文教科書。于是我從暑假就開始閱讀,結果一個學期就讀完了。雖然過程不容易,但這確實也使我養成了閱讀原版書的習慣。在求學期間,我除了學習經典的古生物學專業課程,還修了很多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發育生物學等專業必修課,同時花很多時間閱讀微觀生物學領域原版書,以此擴充知識面。 大三那年,我在一次組會上認識了我的副導師——古脊椎所張馳研究員。張馳老師本科為統計學專業,得知此訊后,我便和張老師請教了一些之前審稿人提到的數學模型。交談中我逐漸意識到與經典的古生物分類工作不同,宏演化分析需要應用大量的統計學方法,如果要想深入理解這些方法的運作原理,還需要學習一些統計學專業高年級的課程。當時我幾乎修完了畢業所需的學分,不過我總是覺得我可能還需要延畢一年,去旁聽自學一些數學系的課程。懷著這種“多學一點”的心態,我開始了本科第五年的學習。 大五的一年中,除了旁聽和自學統計學專業課程以外,我還報名了張馳老師的科創計劃,并開始與徐老師和張老師一起商量博士階段的研究主題。我自己也非常希望將兩位老師的優勢結合起來,做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出來。最終,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確定為《鳥跖類生物多樣性演化整合研究:以鳥類和翼龍為例》,通俗解釋就是使用一些數學模型分析鳥類和翼龍在演化過程中的多樣性變化模式,探討兩者在演化過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一些重要特征在恐龍向鳥類演化過程中的演化趨勢。 余逸倫在Corwin Sullivan的指導下進行三維建模 2020年,我保送到國科大直接攻讀博士學位,開始了我的博士生涯。 與多數古生物學博士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出野外、看標本不同,我多數時間都是坐在辦公室里對著電腦寫代碼。這種工作模式雖然看起來非常輕松,但實際上分析數據過程中處理報錯問題,以及經常需要精讀包含大量數學公式的文獻所需的腦力工作帶來的疲勞絲毫不亞于出野外的體力勞動。 在分析數據的過程中我也會遇到很多新的問題,很多時候也沒有現成的工具可以調用就需要自主編寫函數。在論文投稿以后,審稿人也經常會針對方法本身提出很多問題,如化石保存的不完備性會不會對分析結果帶來影響,我的文章中使用的這種方法與其他工作中的方法有哪些區別、優勢是什么,抑或是讓我們分析更多的數據、提供更多的解釋。回復這些意見往往需要補充更多的分析,這也使得我的每篇論文正文雖然只有寥寥幾頁,但是都附了60多頁甚至上百頁的補充材料。 博士階段的前三年我幾乎每天維持著“727”的工作模式:早上7點起床,7點半到辦公室,晚上2點睡覺,一周工作7天。最終這些成果分別以第一作者發表在PNAS、Current Biology和National Science Review(封面文章)上,我最終也順利提前一年畢業,成為古脊椎所目前唯一4年就拿到博士學位的直博學生。 很多人都說讀博很難,但其實在我通過答辯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是非常平靜的,因為對于一個要以科研為職業的人來說,拿到博士學位只是一個需要完成的流程。 回首過去 展望未來 回首過去這些年的成長,能夠有徐星老師和張馳老師的陪伴是非常幸運的。這十多年來兩位老師的指導也推動我不斷思考古生物學在未來將何去何從。任何一門自然科學都會經歷從博物學傳統向現代科學過渡的蛻變。物理學在伽利略思想實驗時代就完成了這一過渡。現代生物學在現代綜合演化論提出時將更多的數學推演融入到了定性的理論體系中,而在DNA雙螺旋的結構被發現后則全面進入分子時代。古生物學經歷了這么多年的標本積累,也是時候該邁出這一步了。 新的化石證據固然重要,一些化石甚至能夠為一些重大科學問題的解答提供決定性的證據。然而當人們用一塊化石填補了一個空缺后,又會創造兩個新的空缺。在未來的研究中,依據新發現的重要化石對重大科學問題給出解答固然重要,但是整合化石物種和現生物種的信息在統一的框架下進行討論才是古生物學,乃至演化生物學發展的必然需求。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博士畢業是新的起點,我將始終致力于古生物學研究,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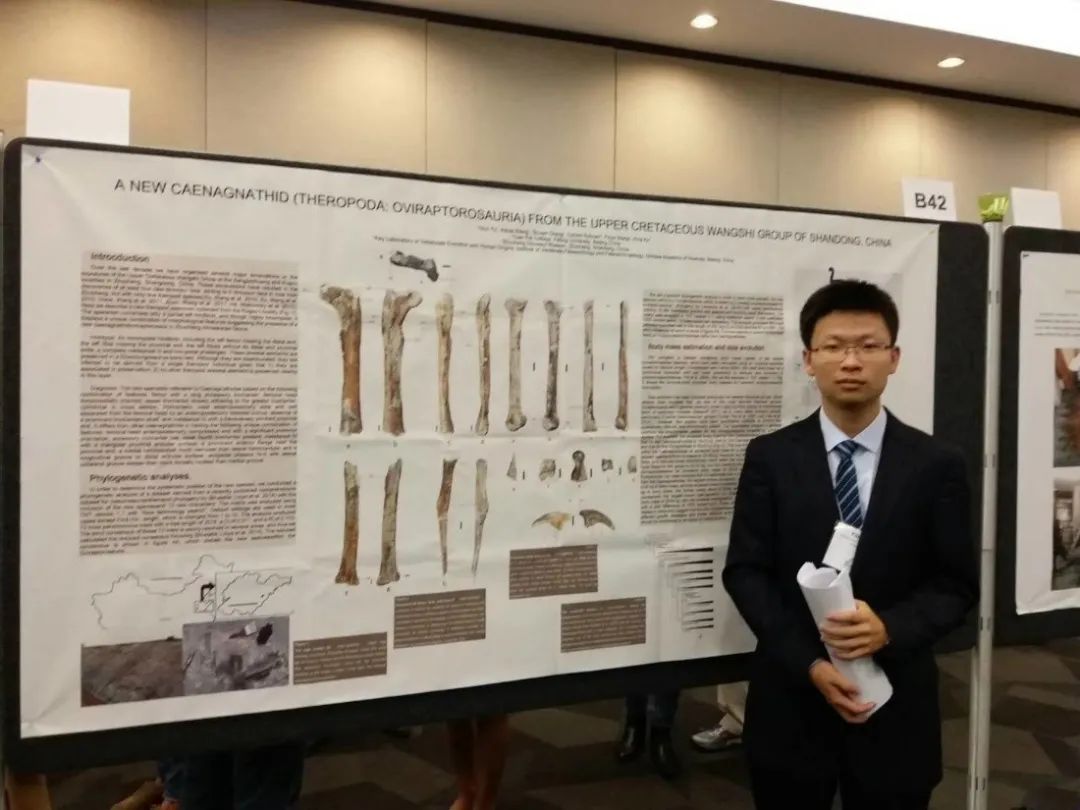




余逸倫與徐星院士和張馳研究員兩位導師合影
(原標題:從北大到國科大,喜歡恐龍的他優秀畢業!)
研究人員利用X射線斷層掃描技術對化石牙根中的生長環進行成像。圖片來源:《科學進展》 科技日報北京8月13日電(記者張夢然)《科學進展》雜志最新發表了一項研究,揭示了早期哺乳動物在漫長“生命史......
近日,在陜西漢中境內一處溶洞內,科研人員發現了一具較為完整的大熊貓化石。綜合頭骨形態、牙齒結構特征及矢狀嵴發育程度等因素,專家初步判斷該大熊貓可能為成年雌性個體,保存的完整程度在國內較為罕見,具有很高......
學科交叉,是當今科學發展之肯綮;科普傳播,則是當今科研工作者們的第二使命。而這,正是國科大2024屆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專業博士畢業生余逸倫這多年來的兩面。在國科大研究生導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學科交叉,是當今科學發展之肯綮;科普傳播,則是當今科研工作者們的第二使命。而這,正是國科大2024屆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專業博士畢業生余逸倫這多年來的兩面。在國科大研究生導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學科交叉,是當今科學發展之肯綮;科普傳播,則是當今科研工作者們的第二使命。而這,正是國科大2024屆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專業博士畢業生余逸倫這多年來的兩面。在國科大研究生導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中新網北京7月27日電(記者孫自法)施普林格·自然旗下開放獲取學術期刊《科學報告》最新發表一篇古生物學論文稱,研究人員在中國發現晚白堊世(約1億年至6600萬年前)中等體型的深吻暴龍新物種化石,命名為......
重慶恐龍屬種又上新,化石距今約1.66億年!日前,科考人員在云陽普安恐龍化石墻中發現一種新屬種恐龍,并將其命名為“朐忍渝州龍”,這也是重慶發現的最早新蜥腳類恐龍。至此,在云陽發現并命名公布的新屬種恐龍......
重慶恐龍屬種又上新,化石距今約1.66億年!日前,科考人員在云陽普安恐龍化石墻中發現一種新屬種恐龍,并將其命名為“朐忍渝州龍”,這也是重慶發現的最早新蜥腳類恐龍。至此,在云陽發現并命名公布的新屬種恐龍......
中新網北京7月4日電(記者孫自法)在中國青藏高原發現的夏河丹尼索瓦古老型人類(夏河人)研究再獲重大突破:通過對白石崖溶洞遺址發掘出土的2500余件動物骨骼進行傳統動物考古學和古蛋白組學分析,特別對其中......
中新網北京6月23日電(記者孫自法)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徐光輝研究員6月23日透露,他領銜的研究團隊最近在江蘇和安徽交界的距今約2.49億年灰巖結核地層中,研究發現一種新的裂齒魚類,將其......